 老鬼《血与铁》
老鬼《血与铁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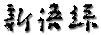
潘屹
老鬼又出了一本新书——《血与铁》。 (老鬼的真名叫马波,我平时叫他马波。但是,为了 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惯,这里还是叫他老鬼吧。) 我给老鬼挂电话,录音器里传出他的沉闷的声音:“ 我出去了。”他签名售书去了,到了西安,又到了南京。 老鬼说,他的书得到了40岁以上的、有相同阅历的人的认 同。 他回来后,我们在甘家口见面。老鬼指着路旁的一辆 轿车说,今年夏天,他去了内蒙,在那里他和他的同伴立 下了这么大的一块石头,上边雕刻着:第二故乡。我说, “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吧?”他说,“是。”这是老鬼 的风格。 今天,人们的眼睛习惯了时尚,社会焦点钟情於散发 着迷幻进口香水味道的风雅女士,和正在生成的或奶油或 典雅的绅士阶层,可是,老鬼给人的感觉还是一块粗糙而 又沉重的石头。他远离时尚。 “当你见到一块历经风雨、在沉默中终於崩发的石头 ,感觉如何呢?”我问的是自己。老鬼递给我他的《血与 铁》说:“你还是先读读我的书吧。” 我们抄写的警句都一样 老鬼的书的风格,我也已经熟悉。记得十几年前,那 是在80年代,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就已经写作了。新闻专 业的一些同学都帮助他抄写他的《血色黄昏》,我也是其 中之一。因为量大,我让我的妹妹也帮助做这件事,她写 不下去,给我退回来,说里边太粗太脏了。难怪,她没有 插过队,下过乡。我不一样,我经历过与老鬼相仿的磨练 的日子。 於是,我可以从容地拿过书,说,“三天就读完,然 后再谈。” 可是,这一次读老鬼的书,居然感到了异常的沉重。 他的每一段、每一章都让我去停顿,去想我的童年、少年 、青春时代。老鬼给我展示了一段历史,真实的。在这历 史里,我们每一个走过那段岁月的人都读到与发现了自己 。 那是一个充满“理想”的年代。老鬼是在中国的革命 英雄主义理想熏陶下长大的。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、《董存 瑞》、《从小培养勇敢精神》、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、《 王若飞在狱中》、《红岩》、《牛虻》、《志愿军英雄传 》、《方志敏战斗的一生》、《古丽雅的道路》、《海鸥 》是他那一代看的电影与读的书。 其实,不只是他,我小老鬼10岁。我对老鬼说,这些 书也是我常看的。其实,也远不止我,远比我们年长的中 国外经贸部女部长吴仪,也说是读了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》这本书,受到了苏联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,才走到了西 北,选择了石化业,并一生未婚。 甚至,我们抄写的革命烈士诗抄警句格言都一样。 “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,生命属於我们只有一次”; “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,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! ”; “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,一切——都是钢铁。 ” 所以,拿到老鬼的书时,一切遥远了的往事又非常清 晰的浮现在脑子里。 他崇拜武松,武松不近女色 也为了这些“理想”,老鬼会不喜欢母亲的高跟鞋、 料子裤,不喜欢自己是作家杨沫的后代,不喜欢自己的姨 母白杨是个演员。也正像不喜欢《青春之歌》中的主人公 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林道静而不是无产阶级或者革命军人 一样,老鬼渴望自己是一个革命者,一个英雄,一个战士 ,他要把自己浇铸成铁。 他作出过许多英雄般的“壮举”:看了《怎样做一个 共产党员》,就伴着骷髅一起睡觉;看了《上甘岭》就尝 试喝泥水;他冒着危险去水库游泳;他周末步行70公里回 家。可笑荒唐吗?走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可能从中发现自己 的影子。 至今,我也执拗地说这些并不荒谬。不合理在於当时 凝造的整个社会氛围,它让个人的人生错位。当老鬼与同 学们想去农村搞社会调查、被农民报告、让持枪的民兵包 围、被当成了美蒋特务时:当老鬼一篇歌颂狗的文章被视 为对其缺少阶级分析时,才让他感到由衷的困惑。 从童年走入少年、青年,开始长大,老鬼被性欲与异 性困惑。但是他的英雄主义思想,纯粹得不容他有一丝世 俗的观念,因此他孤立而走极端。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 一样,他认为性是肮脏的,甚至想要找到一种与春药相反 的药品来扼杀自己的人性。保尔有冬尼娅,牛虻还有琼玛 ,可是老鬼只有崇拜武松,因为武松不近女色。 我们与老鬼都有过那样的时代,把最初青春的萌动视 为丑陋,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肮脏思想,视为见不得人。我 们一点也不知道,人也是自然界的一类,像所有的生物一 样,我们会适时生长,会含苞,会开花,会结果。我们不 知道。 有一首诗,很多人也许都记得:那是我们的年代/我 一说消灭法西斯/你回答自由属於人民/不知道在妈妈生 我们的壮举中/爸爸究竟起了什么作用。 把文革中干的坏事都写出来 不近女色扭曲了老鬼的个性。但是,“吃饱饭比想女 生更重要。”老鬼过不去另一个更大的难关,是饥饿。那 是1960年困难时期。老鬼的革命理想与坚强的意志终於在 姑姑家的一笼菜团子面前摧毁了。 老鬼说,吃是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。於是,饿得 去偷。因为人还是人,离不开人的自然属性。 到了文化大革命,精神释放的老鬼,闯西藏,赴越南 ,搞刀枪,蹲班房。他可以“大义灭亲”:捆绑姐姐,大 字报攻击父亲,揭发母亲,这些把老鬼真正变成了一个魔 鬼撒旦。不仅是老鬼,那个时代,把许多人人性中最邪恶 、最血腥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可悲的是,这一切都是 有革命的理论指导。 老鬼,给了我们那个时代最真切的画面。看到这一节 ,我感到痛苦。当时大多数的青年人都参加了那个史无前 例的运动。但是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老鬼一样,有时是 个恶魔。 我刚接到《血与铁》时,老鬼对我说:不要强迫写, 要自己想写的时候再写。此时,我接到了来自美国的、我 与老鬼共同的朋友的一封信,对我谈老鬼:老鬼的真实在 於,他承认自己不完美,他把自己的弱点展示给其他人, 他恨把它藏起来,他要给大家一个真实。 老鬼自己说,“现在,写这段历史的人很多,却很少 看到当年迫害别人的人敢公开谈谈自己当初的想法、做法 ,好象在有意无意地回避。写《血与铁》也是一个忏悔, 我基本上把自己在文革中所干的坏事都写了出来。”他以 自己的坦诚,毫无掩饰地给了我们一个时代真实翔实的纪 录:理想与残酷、美丽与丑恶、真诚与虚伪、狂热与自私 、坚强与软弱。这也需要至诚与至勇。 我曾认为老鬼偏执。他说,鲁迅说过,当人们要求开 一扇窗户的时候,并不能得到。但是如果要求开一扇门, 那么窗户就可开成了。我以为,他就是那个大声疾呼开门 的人。其实,他的目的,恰好是为了那个应该开的窗。可 是,事实是,不仅作为要开门者老鬼为房屋管理者所反感 ,有时,为开门的大声呼唤甚至为需要窗户的人所倒目。 老鬼们的下一代,青春如何? 老鬼的书是在美国就动笔写的。老鬼说,“在罗得岛 居住时,衣食无虑,与老婆孩子都团聚,却总也摆脱不了 孤独和寂寞。真的,不管你是什么身份,什么背景,混得 如何,发达或潦倒,那沉重的乡思总在冥冥中缭绕。看见 美国的每一样东西都不由自主地想中国有没有。美国被认 为是美的,这美对一个异乡人来说很悲哀。那么那么美, 却是人家的。所以我感觉:我们虽然得到了天空,却失去 了大地。” 於是,这种对比的强烈,让老鬼想起他走过的岁月, 他开始写《血与铁》 在抗战的动乱年代,杨沫写了《青春之歌》,那个年 代,青春尚可如歌。到了儿子老鬼这一代,青春滴滴如血 。老鬼儿子那一代呢? 现在,儿子在美国,生活得很幸福。每年夏天,老鬼 把他迎回中国,去游泳,去马术班,去内蒙古草原。老鬼 有点焦虑地说,儿子的汉语成了问题,管西红柿叫红红的 球,管肥肉叫胖子的肉,这影响了父子之间的交流。不仅 语言,儿子长大了,对父亲笔下的文字表达的世界可能更 有恍如隔世、天方夜谭之感。 也许,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对此应值得庆贺。可是, 话说回来,如此以往,谁又去读老鬼的书呢? 我还记得他第一本书,《血色黄昏》(老鬼的书都与 血相关)完成出版时。他来到我的报社,给我送来了《血 色黄昏》,那本书在报社的年轻人中传看,再也没有回到 过我的手中。 第一本书没有回来,拿走它的是一些年龄远比我小的 年轻人,那时他们拿走它,可能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陪 伴他们。没有电脑、没有迪厅,没有健身房没有保龄球也 没有高尔夫。但是,今天陪伴青年人的东西太多了,因此 我不知道,还有没有年轻人愿意读这样的书。 (《华声》)